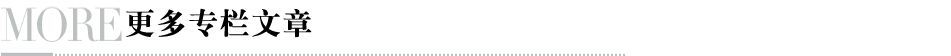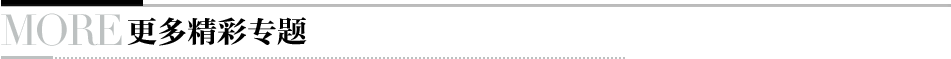1977年,那个冬天我终生难忘,1978年,那个春天也同样难以忘却。转眼四十年过去,应该会有很多人纪念这样一个时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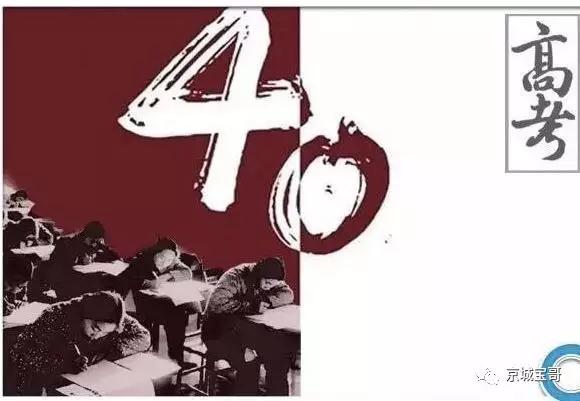
那年我结的婚,旅行回到北京,就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:全国重开高等院校公开招生。平地一声雷,这个消息等待了多久啊!无论是在北大荒还是北京的工厂,每当有推荐工农兵学员机会的时候,心里总是暗暗地祈祷。虽然知道幸运几乎没有可能落在我这样背着家庭“黑锅”的人身上,但是渴望的念头从来没有熄灭。通过考试公开招生,这意味着严格的政治审查不再是第一位,任何人只要在所划定的范围内就可以自由报名。
十年以来的持续自学,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。
自从1966年7、8月以后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再上学读书。“复课闹革命”短暂的中学教育,并没有得到多少知识,然后匆忙地离开学校,走到“广阔天地”里。往多了说,也就是初中的底子。对于这样薄弱的基础,自学一般只能向文科方面努力。理科方向包括数理化的学习比较困难,缺乏指导和实践的条件。1973年以后,我又加上绘画方向的努力,企图走出另一条人生道路。

虽然是自学,在接受大学教育之前,我就已经把几乎当时能够找到看到的中外名著基本读完。包括四部古典名著,国外古典《一千零一夜》《神曲》《堂吉柯德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还有大仲马、小仲马、雨果、左拉、普希金、托尔斯泰、契柯夫、屠格涅夫、肖洛霍夫、马克吐温、德莱塞等等。偏一点的还有波兰的显克维支、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等。诗歌诗词也是中外皆读,李白、杜甫不用说,诗剧《浮士德》《唐璜》、普希金诗集、惠特曼的《草叶集》,偏到莎士比亚的《十四行诗》也读过。革命的就更不用说了,《鲁迅全集》和所有红色小说几乎无一拉下。现在回想,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,能够读到这么多书有点不可思议。这其中有家庭的原因,也有周围的环境因素。家里原有不少,“文 革”后期与父亲一起到“内部书店”也买了一些。周围的人介绍,相互借阅,包括蔡仪的夫人乔象钟是文学研究所的,仅她就悄悄地借给我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书籍。
在当时,是有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文学家的梦想。可以说,这辈子读的小说,大多是大学之前,上学以后小说很少读。那个时期还读了很多的哲学、美学及文学理论著作,包括马克思、恩格斯、黑格尔、费尔巴哈、康德等。美学则“师从”蔡仪、李泽厚、朱荻。这些打下一定的哲学文学功底,让我今天仍保持写作的爱好。同时,也培育了成为“书虫”基因。
绘画的学习就比较专业了。先是山西大学旁听启蒙,后来回到北京跟着中央美院的一帮子弟画素描。再到东城区文化馆的美术班学习,还不断地出去写生。延安时期的老画家辛莽专门指导,每周一次必到他家交作业。崇拜的是印象派、巡回展览画派。设计的知识来自工艺美院的吴劳,是他让我知道画画之外还有另一种艺术。音乐,则是几乎听遍所有能够找到的西洋古典。有了这样的基础,似乎就等机会来临。

我报的是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”,志愿里似乎还有戏剧学院舞美系等。报名通过,马上进入紧张的考前准备。好在那个时候艺术类的考生不用考数化,不然我就更抓狂了。政治、语文加专业,史地可以不考,没有英语考试。由于工厂里很多人都报了名,涉及面大,领导没有给假,只在考试前三天才给假回家。
复习的时间不长,大致是十月下旬到十二月。先考文化课,文化课通过以后等通知,再考专业课。凭借原有的底子,我高分通过文化课考试。当时一个厂里几十个年轻人参加考试,只有我一个通过。在其后两次七八、七九,加之七七年这一次,一共三次大学招生考试,工厂也陆陆续续走了十几个人,三次下来我仍然是最高分。为此,1980年工厂调工资,居然为此还给我涨了一级。
1977年12月10、11、12日是北京市高考的时间。清楚地记得,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,我骑着自行车早早地赶到了考场。验过准考证后,找到自己编号的位置坐下,脑子一片空白,心脏剧烈跳动。考卷发下来以后,眼光集中的考题上,思绪才慢慢稳定下来,逐渐回到了自己的世界。答完后又检查了两遍,交了卷子走出考场。

专业考试上午素描,下午是图案。那日,天阴着,不大的细雨中还有点雪粒,带来的说不出是压抑感还是舒适感。教室的外面和里面都有些湿漉漉,身上也是潮潮的。走进考场,找了一个比较近的位置,架起画板。考生挤得满满,画板挨着画板。素描对象是石膏像,好像俗称“宙里”,反正是反复画过多次的,心里比较踏实。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看别人,不受任何干扰影响。我知道,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是画不完一张完整素描的,只要比例正确步骤得当就不会有问题。几支2B的中华铅笔一直使到头,时间到点只完成了多半,大轮廓是有了。如果要求画完,于我可能反倒不利。我对于素描最后阶段,收拾成为一张完整的作品,始终颇为头疼。因此知道可以了,虽然没完成还是坦然交卷。
1977年,那个冬天显得特别漫长,充满了期盼和焦急的等待。内心也充满惶恐,惴惴不安,没有一点再干什么的动力。在工厂干活更是魂不守舍,天天眼巴巴的望着邮递员。这也成为自1966年开始,最后一个沉重的冬季。

上学的时候,是乍暖还凉的初春。
1978年3月,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已经开学以后,才接到入学报到的通知,较正常入学晚了近一个月。
能够上学的确比较曲折。初期的名字叫“走读班”,是个编外的意思,实际上这是七七届扩大招生的结果。毕竟中断十年的高考,也就是积压十一届的学生。后来看到资料说,570万人参加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次冬季高考。
没有能够在第一批录取,是有各种不同原因的,我是因为已经结婚的一项。这一年的招生条件明确规定“婚否不限”,这样我才能通过资格审核,却不知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招生条件里有一条“未婚”的限制。我至今不能理解,为什么在这条上与整个招生条件相左。之所以不限婚否完全是出于实际。到1977年,老高中生大的已经三十多岁,怎么会不结婚呢。
也是近年逐渐“解密”才知晓,若不是有人“上访”申诉,包括给教育部写信,我们就不会有后来的结果。我是写了信到工艺美院陈述。入学以后有人回顾告知,我的信是拿到院党委会上读的,当时读到不止一人流下眼泪,“文 革”中的悲惨遭遇打动了他们。其实,同学中有着相仿境遇的不止一个。

那个时候为解决问题避免矛盾,的确还有不少办法。“走读”就是一个发明,而且专利不是工艺美院,全国都有。意思是不住校,不挤占学校的住宿资源,可以扩大招收同城考生。
叫“走读班”,学校实际上并没有让我们“走”过一天去读书,但是“扩招”进来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就这样,我和我的同学挤进了这所艺术圣殿的大门,成为27.3万人中的一员。
永远忘不了,1978年的春天是美好的,天特别的晴朗,一扫十年阴霾。拿到迟来的《录取通知书》并没有觉得晚,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。报到那天刚刚下完一场小雪,蓝蓝的天空夹带着一丝寒意。学校院里的玉兰已经开始萌芽,空气中飘荡着春天的气息。十四个北京青年就这样聚到了光华路上。

那个冬天和那个春天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!我的人生轨迹也由此转折。至今要感谢两个关键人物:邓小平和查全性。1977年夏,在邓小平的提议下,召开了“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”。查全性,当时武汉大学的副教授,一个小人物仗义执言一炮打响,说出了许多人埋在心底真话。邓小平能够从谏如流,当场拍板定下这件改变一代人也改变中国的大事。
1978年,那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天,正是这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拉开了改革的帷幕,开始了中国人民“春天的故事”。到今天,持续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,让中国走到了世界前列。
毕业以后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家火热的建设中,参与并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进程。如今,77、78、79三届学生大多进入了退休时节,应该是基本完成了“上半场”的任务,要进入到“下半场”了。我相信,这一段里大多数人会更加自我,也会更加精彩。
2017年8月6日 于北京东方太阳城
注: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与新浪家居网无关